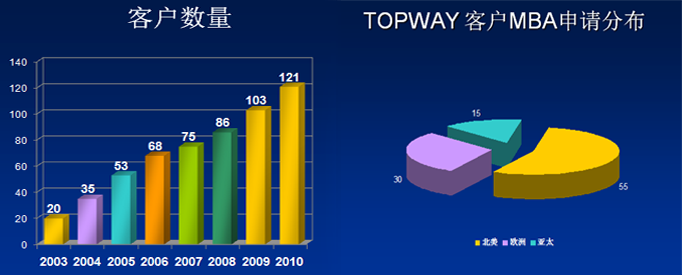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
 
- 精华
- 44
- 积分
- 41210
- 经验
- 41210 点
- 威望
- 4275 点
- 金钱
- 14939 ¥
- 魅力
- 10840
|
通过琳达和冈瑟的事情,我确信,只要有两个顾问就能搞砸一个项目。一个人把大家逼疯,另一个人嘲笑她的演示文稿里的笑话。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了贾斯汀,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我跟他讲述了我们小组里的“逐一发言”逸事。
“啊,那就是常见的‘逐一发言’纳粹。”他说道。“什么?”“每个组织都有一个。这些人从来就说不到点子上,但是他们却强迫大家闭嘴听他们的。”我俩一致认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结识这么多同学确实让人疲惫不堪。面对这么多的笑脸和机械的对话,我们的脸都疼了。这是必需的一个步骤,但是却很令人疲倦。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休息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有许多同学似乎彼此很熟悉,或者有共同的熟人。某些大学和公司的人际网络非常广。对于那些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在人群中流动,直到发现分析论课程中的熟悉面孔。然而只要我回想起对昔日生活的遗憾—工作、地位以及组织结构—我就提醒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无论感觉熟悉练习和主动自我介绍多么难以忍受,这些都是未来更宏大更重要的事情的必要前奏。我提醒自己记住院长的劝告:不要愤世嫉俗。“深红色的问候”这一疯狂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教室,开始了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根源的6 节课中的第一节。我右边坐的是一位苗条的金发女士,眼睛下面有厚厚的眼袋。此前3 年间,她一直在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私人股权公司辛苦工作,专门从事房地产业务。她说自己就读哈佛商学院是为了度假,纯粹之极。她不想学很多内容,但是却期待着休息、解决问题、休长长的假期。我左边的那位曾经做过金融记者,他有些装酷,每天不带教材上课,但却花费整节课的时间告诉我他对讨论内容的一些没有公开的评价。在这样的一堂课上,我们研究了劳斯莱斯的历史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当前形态。在“二战”期间,劳斯莱斯公司被要求为战争生产飞机和发动机。用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公司就组织了一大帮转包商来帮助自己快速可靠地生产。一位曾经在波音公司工作过的女士指出,这样规模的业务外包在她的前雇主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喜欢尽可能地自己承担任务。一位曾经在俄罗斯为一个法国食品集团管理一家工厂的法国人告诉我们:“在我昔日工作过的地方,通常需要6~7 个月的时间来决定分包,然后用5 个月的时间来与分包商谈判,安排妥当,然后另外6 个月的时间开始这个过程。而我们只是生产饼干而已。”
教授让我谈谈是否认为英国处于衰退过程中。我回答说绝对没有。或者说,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出发点。当然,英国不再是昔日的大英帝国,但是英国的经济仍然稳定而具有活力。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却为最不幸的人们保留了覆盖全面的福利安全网。我的回答激起了一些反对意见。一位俄罗斯人说,根据他的经验,英国人懒惰而又无能。一位曾经在伦敦住过一年的年轻的美国银行家说,地铁运转不灵,商店、餐馆、机场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整体水平低得可怕。他说,认为英国仍然是个伟大的国家这一想法是开玩笑。我回答说根据自己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居住的经历,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每个国家也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谁也不能说哪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出色:比如美国和欧洲度假时间的匮乏、法国和英国的全民医疗保障,以及我为了保证家人在美国一年的安全,刚刚签署的1.1 万美元的支票。我可以看到那位美国银行家在对面向我怒目而视,但是下课后那位法国人走过来告诉我他很感激我代表欧洲大陆发言。“对‘鲨鱼’的存在我很遗憾。”他说道。“鲨鱼”是用来描述无缘无故地贬低别人意见的同学的一个常用语。我还没有充分理解到那位银行家的敌意,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被鲨鱼攻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