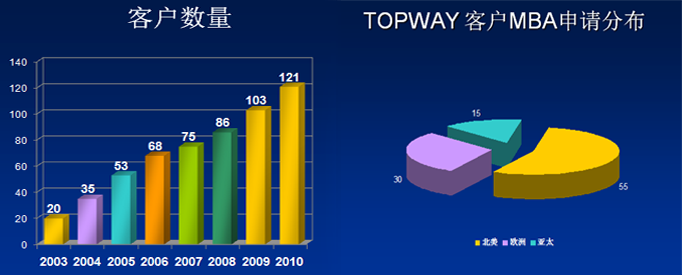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
 
- 精华
- 44
- 积分
- 41210
- 经验
- 41210 点
- 威望
- 4275 点
- 金钱
- 14939 ¥
- 魅力
- 10840
|
“9•11”事件让我的安排乱了套。新闻报道似乎又很重要了。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疲于奔命,要撰写稿件,还要安排从伦敦乘飞机赶来报道这一事件的一队记者和摄影师。后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某一天,我和在纽约的这批英国同行们一起去喝一杯。房间里面挂满了圣诞节灯饰,让每个人因为饮酒已经涨红的面容更加红润。“耸人听闻的事件,”其中一位端起啤酒杯说道,“一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事件赚过这么多钱。”无论何时爆发何种重大事件—不管是政治丑闻、名人受审,还是恐怖袭击造成数千人伤亡—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没心没肺的回应。昔日吸引我加盟记者行业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结正在让我发生改变。此外,就在塌陷之前还站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下,亲眼目睹人们跳出窗口赴死的这段经历也让我思索几百万人都难免会思考的那个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问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洪亮——如果此时此刻生命终结,你会为自己先前的生活感到兴奋吗?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压力。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会在深夜醒来,感觉自己似乎被匕首顶住咽喉逼到墙角,强迫给出回答。你的生活理想吗?你实现所能做到的一切了吗?到底怎样?到底怎样?
作为对我在纽约工作的奖赏,我被报社任命为巴黎办事处主任。搬往巴黎前,我和18 个月前结识的玛格丽特结了婚。婚姻生活和巴黎的工作再次让我放弃了改变职业的想法。当时有一场闹哄哄的总统选举需要报道,还有整个法国需要了解,而在结婚一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奥古斯塔斯降生了。但是那些问题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告诉我,邀请在巴黎的英国新闻界人士来参加午餐会时,大使总是说那是给马喂食饮水的时间。在随后一次的大使馆午餐会上,我端详了一下同桌坐的那些任职时间已经结束却仍然待在巴黎的雇佣文人。他们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他们的穿着打扮似乎每况愈下,嘴唇的颜色也因为饱尝廉价的红酒变得更暗淡了。有个人始终只问一个问题,但是他把这个问题用于任何话题:“大使先生,这一切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大使就拉拉西装的袖口,在精心摆设的桌子对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是从他回答问题的神态,你可以感受到,恐怕连大使馆的前任主人威灵顿公爵在这个不称职的家伙面前都会畏手畏脚。在通宵达旦地喝着红酒和朋友们交谈结束之后,我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无名的恐惧和欲望。抬头看看报纸上的图腾柱,我看到那些中年人在抱怨薪水的微薄和经理的平庸,重提当年在外报道的日子。我担心被召回到伦敦去在办公室工作。于是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写道,时常考虑变化的这种感觉让人筋疲力尽。我已经31 岁,干着一份业内最令人觊觎的工作,然而,我能够想到的却是以后会怎样。我在放纵自我和做出明智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担心如果让工作变化顺其自然而不是主动做出选择,自己会抱憾终生。我在信中提到了曾外祖母,提到了她开创的事业如何在我们家族的失落感中得到放大,从而在大约50 年之后让我们感到怀念。商业曾经使她得到拯救,在这么长时间的回避之后,我感觉商业或许也会让我得到拯救。哈佛商学院的网站上遍布鼓舞人心的诱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强有力的事物”的挑战用深红色大写字母拼写而成,格外显眼。“激情”、“领导力”这样的字眼像标点符号一样装点着网站的页面。上面张贴着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和戴眼镜的教授的照片,教授们双手摆出一副解释问题的姿势,看上去满腹经纶,神采奕奕。在查尔斯河畔,到处是意气风发、充满想象力、敢于领先、勇于进取的莘莘学子。我之所以被哈佛吸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承认,是哈佛的名头。无论哈佛在美国国内多么出名,在国外它的知名度甚至还要更高。无论如何,哈佛依然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学。第二个原因在于哈佛商学院承诺的特殊教育。尽管多数商学院的授课内容大同小异,然而方法和重点却各具特色。在顶级商学院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培养硅谷企业家著称,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以市场营销著称。如果你的梦想是打造或者经营一个美国知名品牌,凯洛格商学院正好合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则是以培养关注华尔街的金融家著称。与此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关注的也是纽约发生的经济变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以培养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用于商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著称,而哈佛大学是侧重综合管理,让你为管理和领导商业的各个层面作好准备,没有任何特别的专门方向。这些描述无疑对上述所有学校都不利,但是因为反复被人提及,因此申请人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个人选择,都很少会无视其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