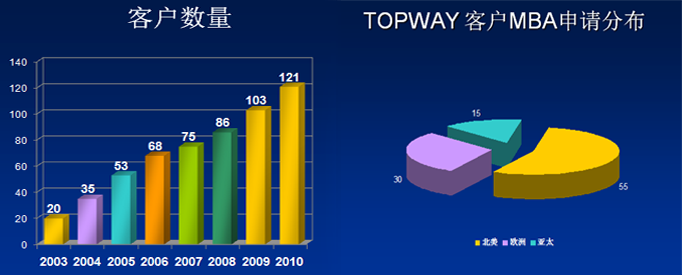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
 
- 精华
- 44
- 积分
- 41210
- 经验
- 41210 点
- 威望
- 4275 点
- 金钱
- 14939 ¥
- 魅力
- 10840
|
接下来的连续六七周时间吧,我们都停留在搞清楚这个project是怎么回事的阶段。在这里我自认为公平客观地说,本来这个阶段不应该耗费这么长的时间,而这个原因主要在Ter身上而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来也有意思,我发现语言对我的障碍主要是在“输出”的部分,诸如presentation啦,或者跟美国同学私下里聊天闲扯啦这样的时候,我总有种“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感觉。然而在“输入”,也就是接受信息的这一部分,虽然我往往不能听懂别人说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但我却能够相对比较明确地捕捉到重点信息,并且在脑子里整合出大体思路。我接着说吧,也就是说,光“热身”,我们就花去了差不多六七周时间。J最开始非常认真,每周我们去公司他都会跟我们Meeting,带我们到小会议室像上课似的专门讲解,还请finance和其他涉及的人给我们资料,又带我们去车间跟负责的人认识交流,等等。可是我们迟迟进入不了实质的工作,我明显感觉到他后面有点失去耐心了。
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很清楚我已经明确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进入车间搞数据搜集了。其间J让我们先作好数据表,我和Ter利用课间讨论,我在下面花了很长时间作出的表格(自认为比较好地领会了project的目的),但是Ter居然硬说是看不懂,非要用她的(只有一个Tab,那么大的一个project她的表格居然只有一个tab,九九乘法表那么大),我知道那个不行,却没办法说服她。拿到公司给J一看,J表情很克制地说:“这个不够,不够……”,我实在忍不住接了一句“concrete”,他马上看了我一眼说“Yes!”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无奈我不可能跟Ter同时拿出我的东西,因为明明是一个team,必须得口径一致。说完这个J就去开会了。我们回来之后这一次又提交了我的表格,可是不管我怎么解释,其实形式很简单,可人家就是说看不懂,我不得不认为,她这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稍微绕回去一点。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有时的确说不清道不明。比如我们这个advisor J,从我们第一次进公司办各种手续时,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印象不错,当然我自己对他也是那种尊重甚至敬畏的感觉――我想新人进入新单位对里面的人可能短时间内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吧,何况是自己的直接上司。说来也奇怪,我对他说的内容,的确领悟得比较快,好像很自然地就能听明白,抓住重点。因此,虽然我说话不多,但只要开口提问,一般都会得到他的肯定和特别认真详细的回答。第一次谈话之后拿到他的邮箱我简单发了个邮件,他很客气地回复了。
记得很清楚的是,除了上面说到的他当着其他人的面肯定了我对project的理解之外,还有一次只有J,我和Ter在小会议室讨论,当时J在白板上给我们讲解,基本上是给出了具体的做法,在说到怎么测算那个大型储存设备的使用成本时,我当时提出,那个成本并不是固定值,而是会根据里面储存的程度而改变的,也就是说,储存的inventory越接近饱和,成本就越低。怕说不清楚,我也拿起笔在白板上划了起来。J完全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赞许我满意。这时我虽然已经看出Ter的茫然和脸色的难看,但一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我当时不说,后面更不会有机会了,下面和Ter的交流要说清楚就更不可能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J对我更明显地表示出了欣赏。一次是在我们提交了我做的表格之后,我们做了一次电话conference meeting。他在电话中看着我的表格提了几个问题,我都明确地回答了,听得出他在电话那头的满意,竟然直接说,H,you are good…当时Ter也在旁边。
还有一次,我和Ter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就开始讨论了,结果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本来这个没什么,可是到了公司以后,我们先见到我们这个Project的另外一个成员(当时J说,考虑到他可能会很忙,为我们介绍另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John和我们合作完成工作,但我的感觉是J本人对我们已经有点没耐心了)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跟John说我们下面要做什么什么,我这就这样被“代表”了,特别生气,当着John的面我又不好意思和她争吵,但是到了办公室坐下来以后脸色肯定很难看。其实我当时没意识到自己的表情,直到J路过我们的办公桌跟我们打招呼,闲聊几句的时候。本来我的座位不靠近走廊,被格挡挡住别人看不见我,但人家是“领导”,为了礼貌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招呼。这时候J很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听他这么说Ter也从座位上扭头过来看我。她的座位在我前面,靠近走廊,我本来只看到她的后背。我说没有,随便聊了几句就坐下来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脸色肯定很难看。
本来也就是这样。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正低头在座位上查我带来的统计资料,突然感到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诧异地扭头一看,原来就是J站在我的座位旁边对我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下。我马上站进来,尽量轻地跟他从我的座位后面绕出去(也就是不从Ter的座位旁边经过),但我眼角地余光还是看到这嗅觉灵敏的家伙已经从座位上扭过头来,我当然装作没看见。唉,不消说,我当时的心情那是十分激动,小鹿乱撞哪!我就怀着砰砰直跳的心情跟J走到了小会议室――哎,我那激动的心情啊!虽然现在事情过去久了(尤其是有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感觉了,但当时还是激动啊――因为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是被另眼相看的,在之前郁闷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关上小会议室的门,J问我对目前的Project感觉如何,有什么想法。虽然他没有直接问,但我凭直觉他一定察觉到了我和Ter之间发生了龃龉,想安抚我一下。我呢,一方面是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另一方面现在想来我怀疑自己当时在潜意识中是不是有点恃“宠”撒娇的成分(待考,呵呵),就干脆来了个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把我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当然,我还不至于说Ter的坏话,一来我不是那种人,二来我要真是那么做的话不免让别人看低了。所以我只是半开玩笑但绝对真实地说我自己都快失去信心了。我说我本来觉得我们不应该花这么长时间在这个阶段,等等。J说能理解我的感受,说他也觉得Teammate之间的合作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等等,当然最后还说了鼓励的话。
本来我的话也谈的差不多了,这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好像是对方提醒他马上要开会了什么的,他对着听筒说“我正跟H在小会议室谈话马上就来”什么的,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开门出来了――我为什么提到开门关门,是因为就在开门的第一时间,我看见Ter就站在门口。因为与这间小会议室隔一道不宽的走廊对面秘书Me办公桌,Ter就站在她的办公桌旁边跟她聊天,眼睛却盯着我们出来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可以肯定当时J接到的电话就是Me打的。再往深里猜想一下,一定时当时Ter看到我和J离开,故意假装跟Me闲聊,借故找J找不到,要Me帮她打一个电话的――因为后者不一定看到我和J进会议室了。就是写到这儿的这一刻我才想到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可惜当时我根本没往深处想,只是觉得怎么这么巧Ter刚好站在门外看我们出来。事后当然Ter问我J跟我说了些什么,我就说他可能是看我状态不好吧问我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就这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