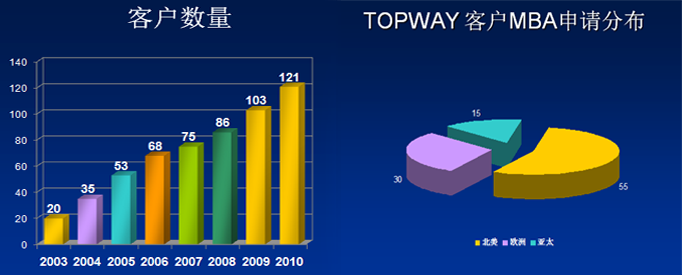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
 
- 精华
- 107
- 积分
- 46748
- 经验
- 46748 点
- 威望
- 4346 点
- 金钱
- 20246 ¥
- 魅力
- 13746
|
施塔特的前世今生
选择从建筑的角度审视MIT,源自今年6月刚刚去世的MIT建筑与规划设计院前任院长、“智能城市”的倡导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建筑物不只是提供我们栖身的地方,它也向天下昭示我们是谁,我们期待成为什么。它同时也应该激发我们去实现人们的愿望。它应该更明确地表现创新的精神、社会的期待以及冒险的思考,而这些正是MIT的特色。”
对于不那么熟悉MIT历史的外来者来说,施塔特中心是一个现在式。人们看到的,是它与MIT所有现有建筑全不搭调、“像被锤子砸过”、“仿佛永远未完工”、“随时都会倒塌”的外观,是它曲里拐弯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帮助才能从洗手间安全返回办公室”——出自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文森特·陈(Vincent Chan)之口——的迷宫般的内部设计,还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传奇——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密码专家罗纳德·李维斯特以及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从MIT的历史看,为施塔特中心赋予特殊意义的,却是它的过去式:它是在20号楼的原址上建造起来的。
20号楼可不是寻常所在。“二战”期间为MIT赢得全球声誉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便设在这栋为满足美国政府军事需要紧急建造的简陋临时建筑中。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底,在阿尔弗雷德·李·鲁米斯(Alfred Lee Loomis)的率领下,辐射实验室承担了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几乎全部微波雷达的研发和制造工作,并研发出了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LORAN。正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突出技术优势,美国海军才得以成功肃清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附近的活动,并于1944年成功实现扭转战局的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9月时,美国政府拨给MIT用于微波雷达研制的经费高达每个月近500万美元,相当于MIT“二战”前整个学校全年的经费。最高峰时,受雇于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达3897人,而这上千人的活动中心,便是20号楼。
20号楼并不好看。弗雷德·哈珀古德(Fred Hapgood)在他关于MIT的《无尽长廊》(Up the Infinite Corridor: MIT and the Techn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写道:“这楼太丑了,简直叫人叹服。它比校园里所有其他的难看建筑物还要丑上10倍。”但是,对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栋虽不好看但却相当合用的大楼却远远没那么糟糕。MIT电子研究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负责林肯实验室的阿尔伯特·希尔(Albert Hill)就说过:“搬进20号楼后,我们实验室的可用空间一下子大了两倍。”主要原因是20号楼是临时建筑,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实验需要调整内部空间。而在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罗姆·莱特文(Jerome Lettvin)的眼中,20号楼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其中却神迹屡现。
如果从时间点上看,辐射实验室和20号楼的黄金时代,的确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在辐射实验室之前,虽然MIT已经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它还不是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它的主要教育目标,依然遵循着罗杰斯时代定下的方针,也即更加强调“手”的训练,旨在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机械业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曾经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回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等基础科学系仍几乎是完全为了迎合工程学学生的兴趣而设立的。“所有这些系都被看做‘服务系’,是工程师们开车进来,把他们的油箱加满初级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课程的加油站。”在“二战”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MIT工程学与基础科学的师资比一直保持在85%比15%左右。
“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拉丁文写作Mens et Manus),这是MIT广为人所知的校训,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它的作者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在这本书中,斯特拉顿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斯杰莱德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前身、成立于1796年的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Instituion),一直被认为是英语国家中第一所理工学院。这所大学的校训是Mente et Manu,与MIT的校训相差仿佛。鉴于美国大学向来有效法英国大学的传统,斯特拉顿开始时以为,MIT的创始人罗杰斯也是从安德森学院的校训中获得的灵感。然而,当他向斯杰莱德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求证此事时,却得到了恰巧相反的答复。历史档案显示,直到1912年,斯杰莱德大学的校董事会才通过了“Mente et Menu”这一校训。而提出此项动议的院长,其实是从一封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来信上的MIT校徽中得到的启示。
回到罗杰斯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在那个被美国教育学家莱曼·亚培(Lyman Abbott)形容为“英国模式的学院培养绅士,德国模式的大学产生学者”的古典精英教育传统仍深入人心的时代,敢于提出“大学教育应当是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国生活所做的技术准备”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理念,并且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这本身便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而格外重视“手”的方面,也是当时情景下矫枉必须过正的由来所然。必须看到,在当时,虽然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一些以满足工业革命背景下现实需要为目标的培训项目和学院,但受制于传统“精英主义”和轻视动手操作能力的羁绊,这些学院始终未能取得可以与罗杰斯的MIT堪相媲美的成就。仅仅成立3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目便已经是哈佛劳伦斯科学院的3倍,这种差距不断扩大,一直延续到1873年的经济恐慌时期。在那之后,虽然差距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生人数上依然一直大幅度领先。
但是,作为一所缺乏传统却勇于创新的私立大学,MIT在创立伊始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却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曾经数次险些为财大气粗的哈佛所吞并。1917年,当美国卷入“一战”后,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风行的“如果最高尚的道德便是为民主社会服务,那么对于教授和大学来说,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投身于服务这个国家的事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更多政府资助的需要,当时的两任校长斯特拉顿和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先后对MIT的教学方向做出调整,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工业生产和军工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一战”期间,MIT便承担了大量美军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和无线电工程师的培训任务,使得整个学校都俨如一所军营。“一战”结束时,5000多名MIT学生和校友在军队中供职,还有2300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文职官员。然而,伴随“一战”而涌入校园的大笔资金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枯竭。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飞机制造公司纷纷裁员,以往炙手可热的航空系毕业生也开始找不到工作。1932年底,由于捐赠收入大幅度下降,MIT不得不把月薪500美元以上的职工工资少发10%,保留待补。向学生征收的学费也增加了。
在这种痛苦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中,MIT的决策层逐渐发现,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创造新的技术应用方向。由此,MIT开始调整工程学和科学的比例,直至达到“二战”后相对较为均衡的1∶1状态。正是从这时开始,MIT后来扬名天下的基础科学院系——经济学系、语言学系、计算机科学系、数学系——吸纳了一大批相对寂寂无名但却相当有天分的年轻人,不过十几二十年后,在这些人中,便涌现出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学大师。而当辐射实验室战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宣布关闭时,它在政府和军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及深厚人脉——“二战”后,在美国军队中服务的MIT校友总数8776人,占当时在世校友的1/4,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使得来自MIT的声音在整个国家的科学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种种因素叠加而成的高潮,是1945年7月,出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MIT前工学院院长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那份战后科学研究规划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Endless Frontier)。它的直接结果是战后十几年中,美国政府对美国高校的研究资助几乎增加了100倍,而在获得研发经费数额的名单上,MIT永远遥遥领先。
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研究资助强化了MIT在理科和工科研究上的霸主地位,也催生了这一时期像雨后蘑菇一般在MIT校园里钻出来的充分体现“多快好省”精神的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然而,与资金一同到来的,也有政府和军方的阴影。根据萨缪尔森的回忆,那时候,配备武器身着便衣的保安人员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守卫着几个“机密”区域,阻止那些没有安全许可证和身份证明的人溜入。MIT的2000多名本科生全都要加入后备军官训练营,学习军事课程。在图书馆里,甚至划分出专门的区域,只有拥有安全许可证的研究者才可以进入。
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本应踌躇满志的MIT校长斯特拉顿却显得深怀忧虑。他说:“我们出生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我们的孩子将会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长大成人,我们也几乎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步调甚至比变化本身更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他已经感受到了在校园里氤氲的反对政府对学术与研究自由干涉的压力,而这种暗地里逐渐扩大的裂痕,对于此时还绝对依赖“冷战经费”的MIT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当此之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被仿制,就连以色列,也成立了以其为范本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对寓居美国和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大抛橄榄枝。更不用说,在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俨然与MIT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MIT最引以为豪的航空航天领域,虽然MIT仍在载人航空上占有优势,但在火箭推进领域,加州理工学院班底的JPL却后发制人,在经费、人才和研究项目上与MIT展开激烈竞争。而在新兴的电子产业,加州的硅谷虽然此时远不如被欢呼为“麻省奇迹”的128公路那样先声夺人,但却也步步紧追,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战后经济的发展,再度像罗杰斯创立MIT之时,呼唤一场新的大学社会职能的转变。大学科研体系扩张带来的科学活动的加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来支持现有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武器和军备,也需要研究者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除了扮演学者的角色,还要当好熟悉市场规则、认清市场方向的“学术企业家”。
很难评价在第一次大学革命中拔得头筹并创立了研究型大学这一大学类别的MIT在这第二次革命中的成败得失。但毫无疑问,几十年过去后,1998年,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Vest)和他背后的校董事会在赶超者的压力下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变革的力量。在例行的校长报告中,韦斯特说,他要强化MIT本科教育的力度,探索能够满足新的研究和教育方向的组织形式,让MIT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以及与企业界达成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韦斯特做了什么?一次接受MIT校报记者采访时,韦斯特说,只要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是那个一手推动MIT开放式课程网页的老头儿就行了。通过将500门MIT相关核心课程的教材免费放到互联网上,韦斯特创造了网络时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新典范——“在互联网的时代,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再是随时面临修正的知识本身,而是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然而,我们的视野也不应漏掉韦斯特任期内也为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增添的几栋极具争议也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便是几乎处处颠覆20号大楼传统的施塔特中心,另一个则是位于西校区的本科生宿舍——绰号“海绵”的西蒙斯楼(Simmons Hall)。
“海绵”里的地狱生活
编号W79的西蒙斯楼建成于2002年,总造价7850万美元,有MIT最昂贵的学生宿舍之称。这栋拿了2003年美国建筑师研究院荣誉奖的宿舍楼最大的特点是窗户多,平均每个房间有9个小窗,每个窗子上有一个单独的小窗帘。据说每天花在开关窗帘上的时间就要5分钟以上。更有趣的是,据说当西蒙斯楼的设计师史蒂芬·霍尔(Steven Holl)在一次晚会上被人问起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无脑的设计时,他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MIT的学生不睡觉。”
某个MIT学生社团的新生介绍小册子上登过一篇文章——“让你在MIT看起来不像旅游者的N种方法”。列出的几条,包括知道IHTFP这个缩写词的含义是“我恨这该死的地方”(I Hate This Fucking Place);“I am major in 2”的意思不是“我很二”而是带点炫耀色彩的“俺是机械工程系的”;至少会唱两句“工程师的祝酒歌”——“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工程师;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喝光40杯啤酒”;千万不要穿带MIT字样的套头衫在学校招摇过市,有海狸图案的T恤或帽子却但用无妨;以及,MIT 失眠课程101——“工作、睡觉、朋友,你只能选两样”(Work,friends,sleep-pick two)。
世界名校中,以天才学生著称的大学不知凡几,但令MIT与众不同的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勤奋的天才”。要想拿到那枚著名的有海狸图案的毕业戒指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理工地狱”(Tech is Hell)的说法,也绝非浪得虚名。“海绵”的绰号固然是因为西蒙斯楼多孔的外形而来,但其实也道中了MIT学生只能不断自我压榨的真相。
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许多MIT学生都有偷偷酗酒的解压习惯。而西蒙斯楼的兴建与MIT最近的宿舍改革,其实便源自一起因酗酒而导致的悲剧。1997年9月29日,18岁的MIT大一新生司各特·克鲁格(Scott Krueger)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悲剧发生前,他刚刚加入MIT的Phi Gamma Delta兄弟会,为了向“老大哥们”表示一下,克鲁格开怀畅饮,不想却以悲剧告终。由于事故发生时克鲁格住在位于波士顿Phi Gamma Delta兄弟会的集体宿舍中,MIT需承担连带责任,最后,MIT向克鲁格的父母赔偿了600万美元,其中125万美元用于设立克鲁格奖学金。所以有人说,西蒙斯楼的造价,还应该再加上475万美元。
克鲁格事件后,MIT决定,不再允许本科生到校外住宿,而为了解决住房不足的问题,才有了西蒙斯楼的兴建和其他一些宿舍的修缮。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后被媒体广为抨击的大学兄弟会问题,却并无声响。闯祸的Phi Gamma Delta虽然自此被取缔,但其他兄弟会却一如既往。比如著名的“青楼”(Green Hall),这栋由格林夫妇捐资兴建的宿舍楼,因为住的都是女生而被戏谑的中国学生冠以此名,便被改成了 Kappa Alpha Theta姐妹会的专属宿舍楼。
对兄弟会姐妹会格外开恩的做法,固然可以理解成对传统的尊重,但作为隐喻的“团队”、“等级”、“忠诚”等元素,却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不断弃旧扬新的表象之下,深藏不变的核心价值。它就像MIT东区校园的众多新旧建筑,尽管外表看上去差别巨大,但在这些楼中,均有通道彼此连接。而这样设计的目的,便是促进各学科各部门的交流,使得沟通不至于因为外界的雨雪阴晴和物理间隔所妨碍。
这种团队合作精神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或许便是大学中的恶作剧。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夜间攀爬标志性建筑并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这更多地体现为个体的单打独斗。而在MIT的众多hacking事例中,皆非有团队协调密切配合所莫办。事实上,一个MIT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便是,许多经典的hacking事例,便出自特定的几个兄弟会手下。有些著名的MIT轶事,比如哈佛桥上的“斯穆特”单位,真相不过是1958年的时候,Lambda Chi Alpha兄弟会的人捉弄刚入会的个头最小的奥列佛·斯穆特(Oliver Smoot),拿他当人肉尺子丈量哈佛桥。细细想来,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像它初听时那么轻松好笑,根据斯穆特的回忆,快到桥的终点时,不停站起趴下的他已经累得不行,是被其他“老大哥们”在地上拖着量完最后一段的。
这种工业社会对待人如机器一般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MIT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随时创新,随时根据社会的需求变化,随时做好准备给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之时,每5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中,便有一个是他所在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裁。仅在马萨诸塞州,便有75家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所创立。而最新的数据显示,MIT的毕业生开办的公司在全球雇佣了110万优秀人才,每年创造2320亿美元的价值。
但这种功利、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的传统,也令MIT成为一个“此地不留爷”的不那么令人喜欢的地方。它可以在犹太人在美国最受排挤的时候录取大量犹太学生,也可以让二十出头的纳什当一个“娃娃讲师”,三十出头的钱学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它却留不住像费曼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然而,这到底是MIT的错,还是一所为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学所依托的环境的错呢?
无论如何,这就是M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