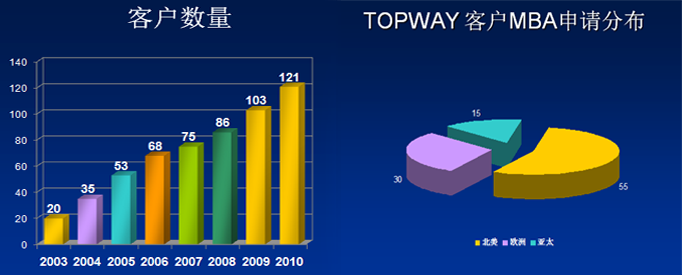2007年的3月28号,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收到UCLA的录取信。那时候我正在给一个洛杉矶的房地产公司打工,做的是重复劳动的房产估值。那天我高
兴坏了,因为这意味着那年的秋天我再也不用继续给我的老板打工,指望着他能给我多点红利。可是,我却一直要按捺住我激动的情绪,因为像很多想要申请的上班
族一样,我是瞒着我的老板申请MBA的。
我那时工作的公司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大概公司里也就20-30个人。我是在没有任何金融背景和房地产背景的情况下进入这家公司的。老板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的一个亲戚跟他的哪个亲戚认识(我至今也没搞清楚),然后面试的时候看我还算机灵,就同意培养我,那是真正的从头开始培养。我是彻头彻尾的文科生,这倒不是说我的理科不行,实在是被中国的文理分科搞得没了脾气,想多学点数学都没机会。幸好我是个勤奋好学又天生敏感的人,老板在培训我的时候,我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不懂的地方都会很仔细的问,这样才算把房地产的基础给打扎实了。后来的技术都是一个公司的台湾合伙人,跟我很聊得来(平时花时间看的《康熙来了》是我们聊天的一大部分主题),才不厌其烦的手把手教我,每次做出来的东西都给他检查,这份需要房地产金融背景的MBA才能干的工作让我这个平庸至极的小女生take了下来。
我在这家公司的责任是用一个叫做Argus的软件,把老板或者老板合伙人弄来的房产和信息一点一点输进去,然后算出一个合理的价值,老板再决定是不是值得投资。通常从broker那里拿来的房产价值都是bullshit,我们公司需要自己重新value它。比如我收到一份30个单位的公寓楼的资
料,broker会告诉我这栋楼最近几年租金的收缴情况以及每个房客租约的长度,维护费用,各种税费,空置率等等很多信息,我把所有可以找到的信息都填进去,然后再用一些假设,比如某个百分比的通胀率之类的,最后算出这个公寓楼的正确估值。如果价值跟broker给的价值比相差很多,那么老板就会瞄上一眼,如果真的可观到他觉得这买卖值得认真讨论,才会真正地去开个会研究一下。不过大部分时间,买卖的决定也不在于我们部门的计算,而是老板的“灵感”,或者英语叫
“gut feeling”。
两三年下来,虽然钱也没有少挣(不好意思,也没多挣),活也没有少干,我却总是忧心忡忡,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到我要离开的时候,公司里的人从我这一层到老板这一层的距离只有纸那么薄,可是却永远捅不破。这是很糟糕的,我的事业一直要这样下去吗?我那时才20多岁,虽然也有人在我这个年纪就开始
相夫教子,可这却远不是我的理想。我的职业之路看似稳定通畅,实则艰难崎岖。
于是我就开始偷偷去老公所在的学校UCLA的Anderson商学院蹭课。好死不死,蹭的课据说是Anderson最好也是最难的课之一Cost
Accounting,是一位好像每年都得“杰出老师”头衔的老师开的。那时候的我有一些会计底子,却没有好到可以听懂他在讲什么。我记得很清楚,这位老师喜欢固定座位,开学第一节课就让大家写了张”seating chart”,
在那同一个学期,我还跑去听了另外一门课,叫做Financial Accounting,
我当时以为是Accounting的另外一个分支,可是听了大概几节课才发现根本就是基础会计课。上课的老师口音有点重,可是很好笑,每次见他都穿着西装 短裤和花衬衫,很像要去夏威夷的样子,腿比女生都要细,而且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叫名字拗口的同学。他的会计讲的很通俗易懂,这在当时的我听上去是比Cost Accouting舒服的多的一门课。 可惜后半学期因为一些别的事情就没有坚持。
在那一个学期以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读MBA的想法,而且把UCLA封做Dream School,
因为我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过老师的教学风格,也跟很多的学生聊过,觉得他们的学生都很年轻,很愿意组织活动,很活泼的样子。再加上家庭的原因,UCLA在当时的我看来,也就是比哈佛和斯坦福差一点的学校,而哈佛和斯坦福我是从来没有指望可以申请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