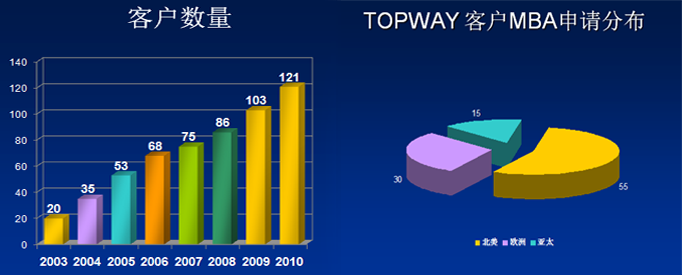很多从中国来的人,对美国大学校区竟然没有用围墙圈起来这一点印象深刻。我刚成为大学“新鲜人”时,也不禁又惊又喜。 我在美国上小学、初中、高中,校舍都基本上全封闭:学生们早上进了校园,大门就上了锁,学生不得出外,外人也不得入内。要是硬推门出去,就会红灯闪烁,警铃大作。学生有事要出门,得向老师申请,签发一张许可,否则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在走廊上楼梯上,就被巡逻的校警或者老师截住了。
之所以如此戒备森严,原因很简单:安全问题实在令人忧心忡忡。看看电视、报刊上报道过多少中学生持枪滥杀的可怕消息吧!
进了大学,一切都不同了。美国大学全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将校园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围墙,更没有什么门卫、没有对来访者一一登记、察看证件和介绍信的手续,学生随时可以扬长而出校园,市民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校园——不,根本不是什么“进出”校园:校园就与城镇彼此交错渗透,校园就是城镇一部分,城镇也是校园一部分,学生走在城镇马路,市民也走在校园小径,教室窗外就是匹萨店,杂货铺对过就是电脑房。我可以在半夜三点钟对着电脑写作业写得脑袋和指头都发木时,与同学三五成群去光顾彻夜亮灯的咖啡馆;也可以在周末睡到日上三竿时爬起来,到拐角处的小店租几盘录像带回来放松放松……
美国许多顶尖大学设在风景幽雅的湖畔山麓,远离尘嚣,鸟语花香,琅琅书声声,学生们可以专心攻读学业。耶鲁却很不一样,老师学生似乎最不可能有“身在世外桃源”的感觉了——每时每刻,都与芸芸众生近在咫尺嘛。
不过,在这没有围墙的校园呆久了,我对学校和城市、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观察,才发现情况远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校园安全——棘手的难题
我上大学三年级那年晚秋的一个周末,打开电脑,赫然看见校长写给全校师生的一封电子邮件,那标题一下狠狠地打进我的眼睛:“悲伤的消息”:“耶鲁大学的全体师生们,我十分悲痛地告诉你们一个悲伤的消息。昨天晚上约10点钟左右,在离校园北部约一英里处,四年级学生苏珊·卓文被人从背后用刀刺死。现在,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苏珊昨天晚上动向的线索,请尽快与警方联系。”
这一惊非同小可。苏珊被刺死的地方,并不是治安不好的街区,相反,那里是治安记录良好的所谓“高尚社区”,是耶鲁的教授讲师喜欢居住的地方,而晚上10点,也不是一个“危险时段”,当时还有不少人在街上散步呢。
苏珊的死让全校师生又一次注意到“校园安全”这个令人棘手的难题——尽管警方确定这不是抢劫行凶,校方也引用警方判断一再强调,这是有预谋的杀害,并不能算在校园治安的帐上。报上还举出数据称,1998年校园内的治安案件比1997年下降了50%多——校园里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安全。
耶鲁的校园内素有不安全的名声,学校所在的城市纽黑文在全美国声名狼藉。我来耶鲁之前,听到了不少关于它的治安的风言风语,包括那个著名的以电灯泡来嘲笑纽黑文的笑话。
那实际上是个系列笑话,讥讽了一大批所谓美国名校。这些笑话都以一个同样的问句轮番问各个名校:“需要几个学生来换一个电灯泡?”
从麻省理工学院到普林斯顿大学,“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答案五花八门,理由更是让人捧腹。例如:
哈佛大学:一个学生——他握着电灯泡,全世界都围着他转。
哥伦比亚大学:76个学生——一个换电灯泡,50个举行集会要求不换电灯泡的权利,另外25个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耶鲁大学:零个学生——因为纽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来顺眼些!
注意到了吧:对别的学校,调侃的都是学生的自负、偏激,惟独对耶鲁,嘲弄的却是所在的环境。其实,耶鲁在美国的名校中,不是唯一一个为所在环境头疼的。哥伦比亚大学坐落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哈莱姆区;芝加哥大学曾为日益进逼的黑人居住区深感棘手;宾州大学位于费城市中心,毒贩子、酒鬼就在校园周围出没……这些高等学府,无不为如何处理与周围满眼脏乱差社区的关系而投入很大的精力。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还远不是那么庞杂、那么混乱的大都市呢。
苏珊之死,舆论很自然地联系起1991年的那桩凶杀案:一位耶鲁学生背后中了一枪,倒在了纽黑文一座教堂门外。那一次,凶犯很快被找到,动机是抢劫。随后,“让耶鲁校园变得更安全”的呼声达到高潮,校方增聘了一大批校警,晚上处处可见他们骑着自行车或者开着警车巡逻的身影;校方又花巨款在校园各个角落安装上了闪着蓝灯的公用电话,随时可以直通警察局。还设立了“校内热线”,让深夜回家、心中忐忑的学生打电话呼唤来一名警察护送走夜路——我有次从较远地方回宿舍时也使用过这种服务。那次我打电话叫来护送的警察是个黑人彪形大汉,足有三百多磅,人很和善,笑眯眯的,告诉我他曾经给很多名人当过保镖,现在轮到给我当保镖了。
而耶鲁校舍的安全管理也运用了高科技手段:校区虽然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但每所住宿学院,包括专门给新生住的“老校园”的宿舍楼,必须要用专门的磁卡才能开启楼门;进了楼门后,还要用磁卡至少开启两道门,才能进到个人房间。一直到苏珊被害时节,我一直感觉,说纽黑文治安怎么怎么让人悬心,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没有超出以前我所居住的城镇的不安全程度。
但是,校园安全不安全,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折射到校园内,却是不争的事实:苏珊被害的那个秋天,也正是耶鲁的多事之秋。那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就有一个新生从公寓14层顶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苏珊被害前两个星期,耶鲁12个住宿学院之一塞布鲁克学院的院长、曾担任过美国地质学协会会长,深受学生们爱戴的一位著名教授,突然被联邦调查局搜查了办公室,他随后被逮捕,控以“非法收集儿童色情图片”和“猥亵幼童”的罪名。同学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了苏珊凶杀案,更没有想到,这起凶杀案后来又有了令人吃惊的线索:警方所列出的可能涉案对象中,竟有耶鲁的一名政治学讲师,苏珊曾经上过这位年轻男老师好几门课,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他就住在离苏珊死的地点不远。
不过,这个案子过了好几年了,仍未水落石出。
再回到校园与城镇的关系上来吧。
说起来有点矛盾:虽然小学、中学非常封闭,学校却是城镇的一部分,与城镇息息相关;而大学虽然非常开放,学校与所在的城镇却可能完全不搭界。这是因为:我在美国所上的中小学,都是公立学校,是隶属于所在城镇的,经费完全仰仗所在城镇居民包括学生家长们所交的房地产税;而耶鲁大学是私立的,它与所在城镇、所在州都没有隶属关系,它是纽黑文最大的一个“顾客”。
社会治安只是纽黑文这个破落小城的问题之一,甚至不是主要问题,贫穷才是问题症结所在。城里的居民贫穷,没有购买能力,许多商店、餐馆、咖啡馆自然不愿在这里开业。到晚上举目四望,只有校园一带几条街比较繁华,商店餐馆灯火通明;稍微走远一点,就满目尽是残败破落,昏黑冷清。没有消费和娱乐场所,老师学生们不敢、也没必要去那些地方;而行人稀少,就更加剧了残败破落,昏黑冷清……如此恶性循环,城镇风貌每况愈下。
另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是:城里的居民贫穷,文化水平也低,除了售货员、送货工一类既不大稳定、收入也比较菲薄的工作,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找到更为理想的职位;而因为经济条件不佳,他们为子女的教育投资也就更力不从心。
一边是耶鲁:美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进来的是所谓“尖子”,出去的是所谓“栋梁”,校方财大气粗;而另一边是“黑暗之中看起来才顺眼些”的纽黑文。就算校园没有围墙,城镇街道与校园浑然一体,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社会藩篱、文化屏障、心理鸿沟也是截然分明的啊。
耶鲁大学一向认为纽黑文是自己的尴尬之处,像个讨厌的穷亲戚,甩都甩不开。在耶鲁与哈佛橄榄球赛时,哈佛学生有时也会拣耶鲁的痛脚踩,嚷道:“你们也许是在赢,但你们终究还得回到纽黑文去!”
不过,从我进耶鲁的前几年开始,耶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承认帮助纽黑文摆脱困境,耶鲁责无旁贷。再仔细想想那个换电灯泡的笑话吧,对耶鲁仅仅是嘲笑环境么?“零个学生——因为纽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来顺眼些”,这不也就是暗讽耶鲁没有一个学生去改变纽黑文的现状,让它在光亮下也看得顺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