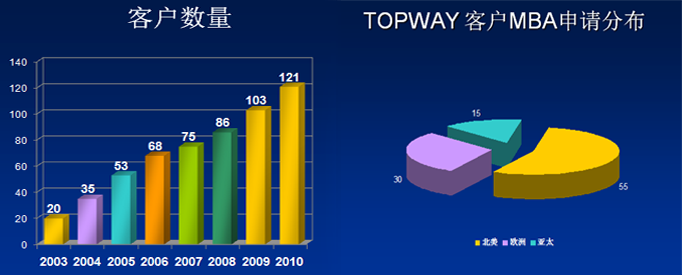|
 
- 精华
- 44
- 积分
- 41210
- 经验
- 41210 点
- 威望
- 4275 点
- 金钱
- 14939 ¥
- 魅力
- 10840
|
Ni大概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之一了。我原以为老天是很公平的,一个人身体不够正常,不够健全,老天大概一定会补偿他一个聪明的头脑,或者其他什么常人所不及的优势。但Ni好像没这么幸运。特别是在统计这一类的课上,他的成绩相当低(我前面说过老师在课堂上是不公布成绩的,每个人的成绩如果不愿意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但Ni是自己提到这一点的),当时上课是我和他坐邻座,从他看着那些内容时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几乎是不知所云的,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了,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也不可能每一个point都insightful,而即使最不聪明的学生,也会偶尔冒出好的见解。在其他讨论case的课上,我就听到过有时Ni的发言其实很有道理。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当周围的人认定一个人是傻瓜时,即使你说的是至理名言,也没有人会理会。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因为废言的傻瓜。
Anyway,他的学习不怎么优秀。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为人,修改,似乎所有的一切也都不讨人喜欢,因此,他没有朋友,而且据我偶尔听到别人口中的他,都是一副不屑甚至厌恶的口气。我实习的伙伴Ter最初和他是一个小组的。说他因为坐着轮椅,动不动手停留在裆部(她觉得像是有意的)很恶心人。我还听到马来西亚女生DT背后公开说Ni上MBA没有意义,言下之意是MBA浪费了资源在这种人身上(这一点我最初听到时就很反感,因为我认为不管不与不是,DT都不是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评判的人)。等等。还有一点,这一点我自己也曾两次注意到,也许是因为他身体残疾因而心理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吧,Ni在偶尔谈到性的问题时会好像是故意似地用一些敏感字眼儿(这些是别人都避免说出口的),让人侧目。还有,因为第三学期重新分组我和他分到了一组,有时一起做功课他生病没来。忘了我和JG因为什么说起他,JG说Ni是一个liar。Liar基本上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人。
也许是基于这种种原因吧,我几乎不敢去想Ni在班上过得有多压抑多难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班上请某外系的教授讲一个case,他要大家自己分组坐在一起。坐定之后,偌大的教室,Ni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默默看着他一个人尴尬地坐在那里,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后来还是教授指着我们这一圈说坐过去几个,我才和苏还有几个人坐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别人怎样,我真为自己当时那种残忍和冷酷感到羞愧万分。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情形,表面上看来对Ni是一个shame,然而实际上,对那些除他和教授以外的所有默默坐在周围的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shame。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冷酷漠然,毫无同情心,我们居然可以那样看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自己的同学一个人坐在一旁――即使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不喜欢他,讨厌他。我还想到,MBA固然是为了培养商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吧,也许在这里坐着的人中间有一天真的会有相当成功的人吧,可是我无法确定一个,或者一群对自己的同伴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究竟会把一个企业,一群人,或者,一个社会带向何处?……也许我想太多了吧。
而我自己,正如前面说印度女孩Pad时提到过的情形似的,虽然对Ni有无数的观察和感想,但我也不愿意和他走得太近(我想也许班上的“扶贫对象”们都有这样的心理),不愿被大家认为我和他是“一伙儿的”。因为那样就等于你自觉地给自己的脑门上贴上了最差生的标签,这不就是人以类聚的原理吗。有一次让Finance课,记不清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我和Ni坐同桌,譬如他认为结论应该是a,而我知道是b.后来讨论结束果然是b, Ni转头对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看来咱们弄错了!我马上硬梆梆地回了一句:我说的本来就是b!后来想想,我当时的潜台词就是: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切!殊不知在班上其他同学的眼中,我可能本来就跟Ni差不多呢,只不过我自己认为我比他强。
就在学习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和Ni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残疾人,不是吗?只不过,他是身体上的残疾人,而我是语言上的残疾人罢了。连苏都说过我用中文说话的时候很聪明,可是一换成英文。。。她不好意思说出下面的话了,可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啊,一个人说话,如果前言不搭后语,期期艾艾,语无伦次,你会不会觉得他可能脑袋也不大灵光呢?所以,我和Ni其实是一样的。我常常想,一个有“残疾”人,不管是身体的还是语言的,如果你没有超乎寻常的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超乎寻常的坚强的意志,你会很容易地最终变成一个心理上的残疾人。当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自信没有了的时候,就会变得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甚至变成一个liar。这样一来,只会加重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否定,然后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假如如JG所说,Ni真是一个Liar的话,我也不相信他天生就是,而是觉得,那一定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奈保留一点自尊而在作最好的笨拙的努力罢了。
也许我想得太沉重了吧。但愿如此。
就在我打了电话的第二天,Ni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他搬到C市去了,在那儿有一份工作,虽然不是他想干的,但毕竟得为了paycheck啊。他说他正在商谈另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成功的话,可能会搬到North Carolina去。我当然希望他能顺利。我们又谈了谈知道的别的同学的情况,一起感叹说,谁能想到我们这么背运呢,毕业这一年多美国经济这么糟糕。他问我是否还去游泳,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下课一起去体育馆游泳的话(但一次也没有真正一起去过。因为我们从没人真正约过,我更不能想象那样一种情景,男女有别倒是其次的问题)。我们约好keep in touch,挂断了电话。刚好是中午,这一天天气非常之好,阳光暖融融的,照得我的房间一片明亮,我的心里也似乎有另一种温暖升起。也祝福Ni。 |
|